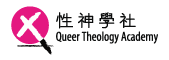拒絕我們是誰
邵家臻
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
青年研究實踐中心副主任
「或許,當前的目標並不是在於發現我們是誰,而是拒絕我們是誰。祇要有權力關係,我們就有拒絕的可能與必須,龐大的權力關係每時每刻都有規定我們是誰。規定以後,便是支配與控制。在權力的牢籠中,我們被規定為機器、工具與奴僕,反抗這種規定,就會被指責狂人、瘋子和異端。拒絕我們是誰,便是拒絕權力強加給我們的非人本質。拒絕,是對牢籠的衝破;拒絕,是主體的屹立和解放。」﹙Foucault,1984﹚。
在何時何日讀過這段說話,我都忘記了。可是,左搬右搬都好,它始終貼在我工作室的當眼處。拒絕,對所有稍為涉及批判理論的人來說,都不應大驚少怪。但今回有所不同,因為它叫「拒絕我們是誰」。福柯不是說:「拒絕霸權」、「拒絕宰制」、「拒絕異化」、「拒絕同流合污」,甚至不是說:「拒絕沽名釣譽」。他的而且確說:「拒絕我們是誰」。餘音裊裊,不絕如縷。
「拒絕我們是誰」不是熟悉的廣告術語。潮流總是諗著“Just be yourself”, “Believe in yourself. Nothing is impossible”, “Stand up for yourself” 的時候,「拒絕我們是誰」就是一種逆襲。它跟每天聽盡的「誰偷去我的乳酪」、「打開雙手得到一切」等正向思想(Positive thinking) 和正向心理學(Positive psychology) 逈然有異。總之,它好像還有點甚麼似的—一種深沉的身份政治策略正在展開。
美國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在紐約書評上介紹福柯的《規訓與懲罰》英譯本時,對「福柯是誰」作了一個很精彩的說法:「他是個令人難以捉摸的人物。他是一個反歷史的歷史學家,一個反人本主義的人文科學家,一個反結構主義的結構主義者。」﹙劉北成,1995﹚是的,我們只能用很多「不是」來形容他─很有學問,但不是學者;對倫理很有興趣,但不是倫理學家;研究語言的法則和意義,但不是語言學家;探勘了鮮為人知的希臘歷史,但不是歷史學家;寫了一本關係古典西方醫學告精神病的重要著作,但也不是個醫學專家……。那位「對規範的逾越」、「對超驗性的指斥」、「對理性的抗爭」、「對詩意的渴望」、「對極端體驗的迷戀」的哲人像是要帶領我們另闢蹊徑,重新思考「我們如何成為我們」這個老問題—關於「我們如何成為我們」,他其實說的「我們可以不是如此這般」這種身份思考。
身份本是一個中性詞。身份認同也並不必然帶來災難,甚至,它還是一個好東西,因為身份認同會給人一種共同體的感覺,是人類生活的泉源。然而這位福利經濟學家Amartya Sen卻提醒我們小心「單一身份的暴力」:「堅持人類身份毫無選擇的單一性,哪怕只是一種下意識的觀念,不僅會大大削減我們豐富的人性,而且也使這個世界處於一種一觸即發的狀態,因為單一的別無選擇的身份認同同樣會殺人」。他回顧1994年的盧旺達大屠殺,當那些黑人被告知自己是胡圖人,而且「我們憎恨圖西人」的時候,「無知的民眾實際上是被套上了單一而且好鬥的身份,由熟練的劊子手帶領著釀造了這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」(Sen, 2007)。
人愛自我標榜,也愛給別人貼標籤,喜歡以局部代替整體。值得反思的是,我們標示一件物品,通常是為了增加其辨識度。然而,當我們將某人貼上一個負面的標籤,並且將其簡化唯一身份的時候,暴力便已經在醞釀。因為別無選擇的單一身份抹殺了人的多元群體特徵與多重忠誠。它像海水一樣,可以將每個族群、每個人圍成一座座孤島,從此孤立無援。Amartya Sen以為:「詆毀他人做法的基礎,一是對他人予以錯誤的描述,二是制造這些是這個可鄙棄的人的唯一身份幻象。」回顧人類歷史,路易十六被殺頭,因為在革命者眼裡他的唯一身份是暴君。猶太人被趕殺,因為在納粹份子那裡他們的唯一身份是猶太人。同樣,在中國盛行階級鬥爭的年代裡,當一個人因為「地主」、「黑五類」、「階級敵人」等別無選擇的單一身份而被批鬥時,他身上所有其他關係或者身份屬性便立刻消失。此時,他不再是一位父親、兒子或者丈夫,不再是鄉親鄰里,甚至也不再是「人」。他只是「寄生蟲」、「剝削者」、「偉大事業的破壞者」等污名的集合體,其他歸屬關係的消失切斷了他應得的一切人道救濟與同情心。
《人‧性II:誰不是酷兒?本土酷兒神學初探》是本本土酷兒理論的傑作。它沿襲酷兒理論對「性別二元思維」、「社會常態化」、「本質化和同質化的身份觀念」的詰問,重新思考「出櫃」、「出軌」、「自慰」、「雙性情慾」、「殘障者的情慾」、「性工作」、「多元家庭」等老問題,讓門裡的她他和門外的你我,透過半掩的門逢交換意味深長的一瞥。
常以為,平庸的心靈從諸事中尋找共同點;精緻的心靈是推敲箇中的差異。書中涵蓋了不同的性小眾類別,稱他們為「酷兒」也好,叫他們為「不雅社群」也無妨,反正用甚麼名稱都只是一種粗疏的分類。不如「拒絕我們是誰」,寧願著眼於生命的妙曼,她們有自己的質感,或濃或淡,或韌或暢。有些生命像文章結構,起承轉合,該凸的凸,該仄的仄,該緊的緊,該疏的疏;有些的音調、凝視、行走則飽含憂思,像條河流,或靜默存在或不絕流竄。要傾聽一個人的生命之旅,殊不容易。這種不易,是因為你若無法投射自己的情感,便輕若身外。
可惜,這個時代「殺氣重」,缺乏察納雅言、包容異己的公民之德或君子之風。
每個人似乎都急於表達,而非傾聽;急於征戰,而非協商。在嘈雜的言論廣場上,相遇的不是人,而是各式各樣的噪音。「變態」、「性癮患者」、「癖」、「無政府主義」、「激進」各種帽子滿天飛舞。傳播學有個叫「沉默的螺旋」的理論,意思是指人們在表達自己觀點時,如果看到自己贊同的觀點,廣受歡迎,就會積極參與進來,這類觀點越發大膽發表和擴散;而發覺某一觀點無人理會或被群起攻之,即使自己贊同它,也會保持沉默。最後結果是意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,如此循環往復,便形成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強大,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發展過程。繼續此消彼長下去,攻擊性及排他性群體遂形成,並以一種「我者—他者」的模式繁衍下去。正如歷史上許多悲劇一樣,被攻擊者/他者被賦予了單一身份,而被排除在整個群體之外。
但願《人‧性II:誰不是酷兒?本土酷兒神學初探》不要坎陷在「沉默的螺旋」之中,落寞寡歡,跼跼獨行。
參考書目:
Foucault, Michel, (1984), The Foucault Reader. Rabinow, R. (ed.) New York: Pantheon Books.
Sen, A. (2007). Identity and Violence: The Illusion of Destiny. India: Penguin Book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