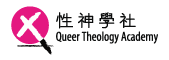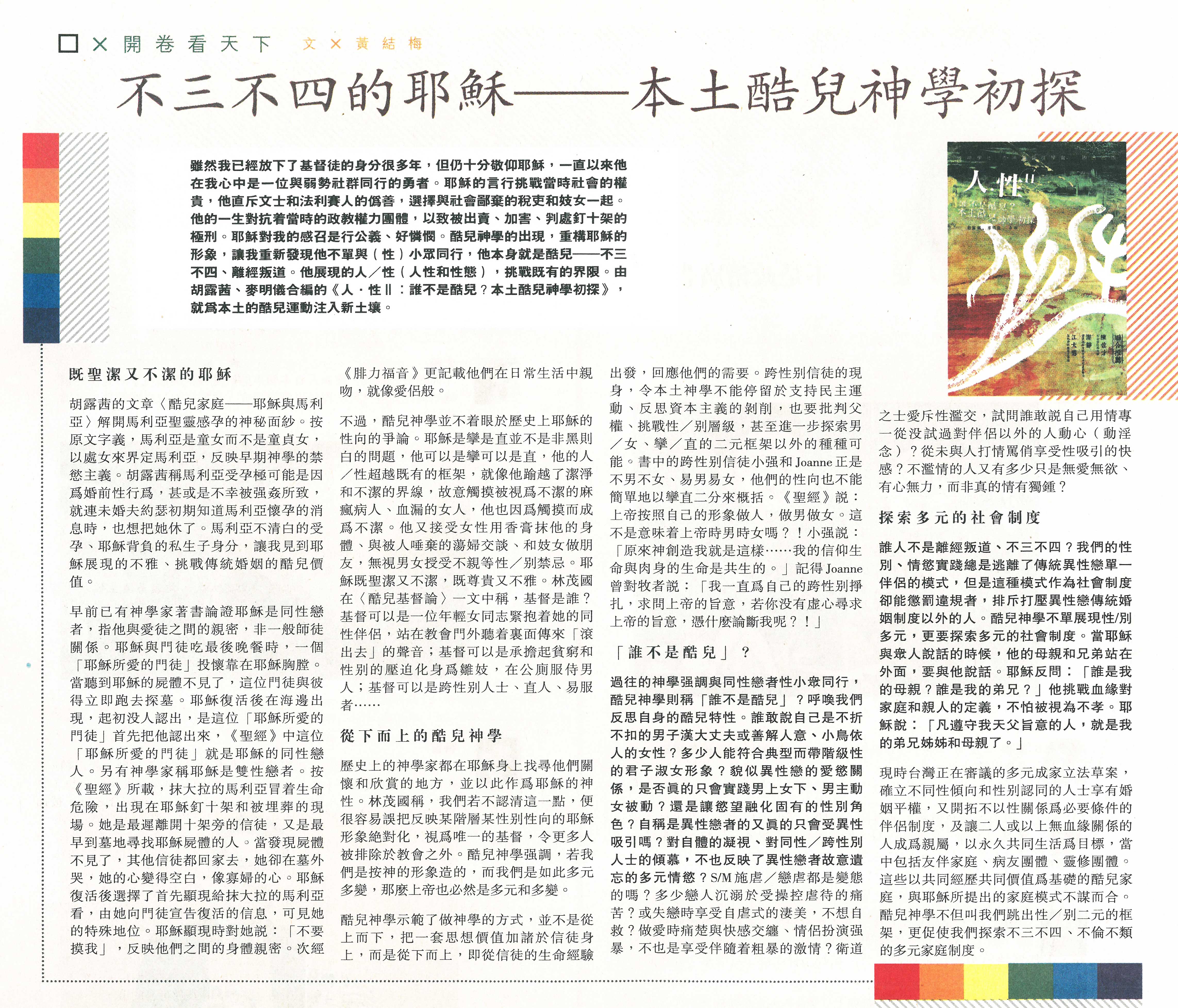拒絕我們是誰
邵家臻
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
青年研究實踐中心副主任
「或許,當前的目標並不是在於發現我們是誰,而是拒絕我們是誰。祇要有權力關係,我們就有拒絕的可能與必須,龐大的權力關係每時每刻都有規定我們是誰。規定以後,便是支配與控制。在權力的牢籠中,我們被規定為機器、工具與奴僕,反抗這種規定,就會被指責狂人、瘋子和異端。拒絕我們是誰,便是拒絕權力強加給我們的非人本質。拒絕,是對牢籠的衝破;拒絕,是主體的屹立和解放。」﹙Foucault,1984﹚。
在何時何日讀過這段說話,我都忘記了。可是,左搬右搬都好,它始終貼在我工作室的當眼處。拒絕,對所有稍為涉及批判理論的人來說,都不應大驚少怪。但今回有所不同,因為它叫「拒絕我們是誰」。福柯不是說:「拒絕霸權」、「拒絕宰制」、「拒絕異化」、「拒絕同流合污」,甚至不是說:「拒絕沽名釣譽」。他的而且確說:「拒絕我們是誰」。餘音裊裊,不絕如縷。